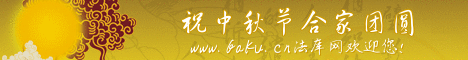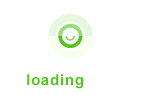核心提示:温情体恤与冷峻思索——读孙焱莉小说张艳梅 近年来,70后作家写作不断突围,逐渐摆脱上一代作家笼罩,形成更自觉的世界表现形态,以及生命表达方式。2013年,70后作家有几部长篇小说,引起文坛瞩目。包括徐...
孙焱莉小说大都沿着家庭生活展开,她不专注于男女情爱的曲折幽婉,而是执着于家庭生活琐碎繁绕。在日常柴米油盐中,呈现出复杂纠结的家庭伦理关系,从中发现人性的多样性。错位断裂伤痕累累的亲情,交织着各种现实利益的爱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内心焦灼和情绪困扰,都表现得细致可感,充满生活气息。在《何处遗失》《女儿》《萝卜灯》等小说中,她写了一些收养或者被收养的孩子。无论是《何处遗失》中的葵花的二妹,还是《萝卜灯》中的成明,还有《女儿》中的姚姑娘,这些幼年离家,或者尚在襁褓中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在别人的家庭中作为养子,或者养女长大。《何处遗失》中的葵花二妹,始终对父母不肯原谅,最终病逝。《女儿》中的姚姑娘,因为养父母去世,重新回到亲生父母家中,然后自己恋爱,有了孩子,又收养了一个孩子,最终原谅了将自己送人的父母,重新回到故乡,回到父母身边。对这种时代变迁中爱怨交织的亲情,对造成这种亲情断裂的社会原因和人性本质,孙焱莉有着认真的思索和执着的表现。
《何处遗失》从葵花的成长历程写起,幼年的葵花孤独寂寞,经常独自在有青砖围墙的院子里跳房子。母亲去了遥远的外地乡下,好久没有音讯。在葵花的记忆里,母亲之前也去过那个遥远的地方,并没带上自己,似乎总有不带的理由。葵花整日被关在院子里,一个人玩,童年记忆是天空、墙壁和盼望父亲的脚步声响起。后来知道还有一个二妹,她不愿意去看她,找各种借口拖延,不是因为她是个冷漠无情的人,而是幼年的经历让她对感情缺少信任,并且她习惯了自己和弟弟的二人姐弟世界。忽然多出来一个人,血缘上的亲人,亲情上的陌生人,她心理上不能接受。作者写出了那种尴尬和不适应。直到终于见到妹妹,葵花并没有什么悲伤的感觉,即使面前这个人身患重病,即使这个人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备受煎熬,故作坚强。当母亲给妹妹一大笔钱时,葵花生气地走到了外面,劈头盖脸对弟弟抱怨:“咱妈真是的,不说病是真是假的,就连人是真是假的都不能确定,乱塞什么钱?你看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光听一个老婆子在这说这说那唱独角戏……向阳突然打断葵花的话:姐,你怎么搞的,别这么狭隘行不?”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原本看起来不是很有正事,不是很重视家庭,整天到处乱跑的向阳,反而更具有同情心和包容性,这一笔,人性的复杂性就出来了。孙焱莉还写过和向阳类似的形象,看起来对生活很随意的人,其实内心有着严肃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立场,就像《清明》中的弟弟秦飞。小说结尾仍旧是母女之间的相依为命。葵花发现丈夫外遇,去做了流产手术。“母亲边哭边说:她没了!我还没抱抱她!葵花一惊,以为母亲知道自己流产的事了。她想说点什么,母亲继续一边哭,一边说,身子一边往下软:你二妹没了!没了!葵花一下子拖住母亲,把她抱在怀里,母亲那么轻,像个婴儿,而此刻她的力量恢复如初,她说:妈!没事的,我在,有我在!”母女同时失掉了自己的孩子。作者写出了人生不得不面对的痛苦,以及自己孩子失去后,葵花对母亲的理解,对亲情的顿悟,亲人之爱仍旧是最后的支撑。《女儿》也是写一个被送出去的女孩子。只不过与《何处遗失》视角不同。《何处遗失》重点在于家人对于给出去的亲人身患重病多年后重新相见的各种表现。《女儿》重点则在于给出去的女孩长大后面对自己亲人的复杂心态和人生选择。十六岁的姚姑娘是边门店老街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当她嘴衔着一根草茎第一次走进通往边门店老街的胡同口时,心其实是浸在油里的,别人却看不出来。姚姑娘是边门店供销社售货员姚老五给出去的闺女。回到自己家的第二天,她就要去投湖。直到姚老五看着自己这个女儿穿着干净鲜亮的新衣服第一次走进边门店供销社,他悬晃着心才慢慢落到了底。后来,六姑娘爱上一个跟随舅舅收皮货的名叫秦关中的南城人。在遇到秦关中那天,姚姑娘找出一家四口在家乡南城海边的合影,那是父亲平反的第二年,照片中的他依然是那么年轻英俊。对少年时代生活的记忆,对养父母的爱,让她爱上秦关中,这个人,是她精神乡愁和心灵乡愁的对应。秦关中死后,姚姑娘带着孩子回到父母家。她对世事和亲人的谅解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