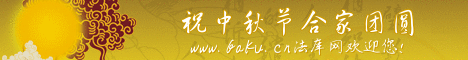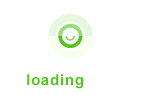小小说
儿子从小就爱好音乐,整天唱唱咧咧蹦蹦跶哒的,上学后,每年在学校唱歌比赛中都是第一名。
在家里每次吃饭前,他就拿着筷子敲碗,即使饭菜端上来了也敲,边敲边唱,把他妈气得多次抢下筷子打他,每次都给他打哭,可咋打也没脸,下次还敲。
每到暑假寒假,他都召集一帮小孩到家里来,在房前或房后,把几个铁桶倒过来放到地上,边敲边唱,把这几个小孩当观众,比比划划,嘻皮笑脸的说着台词,在墙上写着什么什么演唱会,拿个小木棒当做话筒。
十三岁那年,他就会打秧歌鼓了。
那年,我们村组建了秧歌队,打算过春节时给村干部家和附近企业拜年,说白了就是大要饭儿的,图点儿赏钱和烟,领头的来我家要雇他去给打鼓,说每天给二十元,我说钱不重要,别累着孩子就行,这样他就去给打了二天鼓,每次回来小脸都冻得彤红。
每当村里有办丧事情雇鼓乐的,他就去观看,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还时常趁人家不注意鼓捣几下子。
十四岁那年,他爷爷去世了,我雇了鼓乐,乐队来了,可没有架子鼓鼓手,亲朋好友们让他上去打,他说我爷爷死了我怎能打鼓呢,亲朋好友们说,你爷爷生前喜欢音乐,这也算你告慰了你爷爷的英灵,他看了看我,我说你上去打吧。
从来没和谁学过,全靠自误,他上场了,鼓乐队为了照顾他,先演奏节奏慢的,比如‘想家的时候’‘中国大舞台’‘父亲’等,可发现他跟的拍节婉转流畅,轻松自如,便加快了节奏,演奏了‘站台’和’护花使者‘这类快节奏的音乐,他双手双脚配合娴熟,快如闪电,悲情激昂,发挥得淋离尽致,边打边流出悲痛的泪水,参加宴奠的亲朋都过来欣赏,都很惊呀,就连做饭做菜的师傅们也都放下手里的活计,过来目睹这一风彩。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村又有一家办丧事情的雇了鼓乐,他站在弹电子琴的一旁观看了有三个多小时 ,那天是二月份,天很冷,我去找他叫他回家,他说什么也不走。
就在那天晚上,我对他说,如果你喜欢电子琴,我给你买一台,再给你找一个老师,可前提是你必须用心学,你能做到吗?他说,爸,你给我买吧,我不会辜负你的希望,我一定能学好。
那时我的条件很不好,正是养鸡亏损欠下外债的时候,手里根本没有钱,我便找到同学做了二千元钱袋款。
那天是二零零年的三月份,天气咋暖咋寒,我迎着北风,去法库给他买回了卡西欧880电子琴,花了一千一百元。
他放学回来后对我说,爸,今天老师讲的课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你买电子琴的影子了,今天我就盼望早点回家,赶紧看到这台电子琴,说完摸着电子琴爱不释手。
过了二天,我去县里给他找到了教声乐和电子琴的老师,讲好每月八节课,声乐和电子琴一起教,每月一百元。
为了方便和老师沟通,我又花几百元钱安了个坐机电话。
当时学琴很不方便,因为我家离法库十五里,那年公交车只通了一半,他每次去法库学琴先要骑自行车走一半到公交车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法库。
骑自行车带电子琴又很不方便,我便特意焊制了一个琴筐,挂在自行车后边,并告诉他万一骑车摔倒了怎样保护电子琴。
有一次他去学琴,回来时天色已晚不通公交车了,他背着琴在法库北门等车,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车,他就背着琴走了八里,然后又骑着自行车回来的,回来时天已经很黑了,把他累病了,打了好几针,我很心疼。
他学的很刻苦,很认真,每天都能保证四个小时练琴和练发声,节假日都没停过,有时练到下半夜。
半年后他的老师对我说,大哥,这孩子的天赋和接受能力太强了,学半年就相当于我的水平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前途,我不想教他了,我给你们推荐个音乐院校,让他去正规的院校去学吧。
我对他的老师说,我现在条件很不好,每月花一百元钱都费劲呢,哪有钱供他去音乐院校呢,还是和你学吧。
这样,他和这位老师学了一年半,可半年后根本没学到啥东西。
有一次他正在老师家学习,他老师的康平朋友打来电话,让他老师去康平帮忙演出,他老师说没时间去,就让他去,这样他背着电子琴在法库坐大客车去了康平,给歌手们伴了奏,自己也唱了几首歌,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演出,承办方给了他五十元钱,他很高兴,那年他十四岁。
由于他专心学习音乐,所以从此不正经学文化课了,学习成绩迅速下滑,他的班主任找到了我,说你家孩子上课不认真听,整天不知道心里在想啥,天天去音乐室去玩,就和音乐老师好。
我也骂过他很多次,让他在学琴的同时不要误了文化课,可咋说也无济于事。
由于他的老师多次推荐他在法库和康平演出,法库农村的鼓乐队也有很多都认识他了,也都找他演出,他就更不好好念书了,于是辍学了,我也破罐子破摔,不逼他去学校了,我心想你不念也好,如果你真的考上大学我供你还真费劲。
那年他十五岁,正念初一,从此告别了学校。
这时风言风语接踵而至,有人说我是在对他拔苗助长,有人说我不玩儿正经事儿,我爱人也骂我,说我在搞穷欢乐......
干演出这行也不容易,如果是开业庆典或婚礼庆典还可以,都是白天,时间也短,而干丧事情活就不好干了,其实丧事情鼓乐队就是闯江湖,业内人称‘上买卖’,唱戏的要看雇用者的眼神行事,冬天在外边弹唱,前边拢一堆火,后边冻脊梁骨,前边烤脸后边冰凉,冻手冻脚,要干到半夜,还要应对各类酒蒙子搅场,弄不好还打架,所以很辛苦,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每次回来都把挣得的钱交给我,从不乱花一分钱,就这样,他在这种环境下度过了三年,由于冬天弹琴冻手,他的指关节逐渐增生变粗了,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又很无奈。
十八岁那年,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叔对我说,让孩子这样下去一辈子只能挣点辛苦钱,也挣不多少,再说现在婚宴和开业基本都不用乐队了,农村办丧事也逐渐没人雇了,你应该让他去当兵。我便对他说了,他同意了。
可参军有个条件是,农村的必须有初中毕业证,他没有,所以我花钱找人给他办了个初中毕业证。
那年十月份他报了名,兵种是大连海军,接兵的高连长来家访时,问他有啥特长,他边弹边唱了‘军港之夜’,高连长为之一阵,喜出望外,连声说,太舒服了,太舒服了,你跟我走吧。
那年十二月五号,他和高连长在法库坐上了去铁岭火车站的客车,然后换乘火车去大连,在离开法库的大客上,我看见他和高连长坐在一起。
在火车上,高连长没离开他,还给了他一个苹果。
到大连旅顺海军军营后,来自法库的四十名新兵被分开去了四个地方军训,高连长把他留在了身边。
军训很苦,可他从不对我们说,军训刚结束,有一天班长喊他,说文工团来人挑演员,让他去面试,他当时即兴奋又心跳。
面试的一共三个人,他看到高连长也在那里,他用吉他自弹自唱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看到首长们的脸都笑盈盈的,高连长在一旁和首长们交头接耳,微笑着指指点点。
第二天,来了台面包车,一位干事下车走进了他们连部,找到了他们连长,连长领着干事找到他,连长让他打点行囊,跟干事走,战友们帮他把大包小裹装上车,他和新兵战友们告别,面包车把他拉到了大连海军基地司令部宣传处直属演出队。
车开进大门,宣传处刘处长迎了出来,亲切的拉着他的手说,欢迎欢迎,你就是王海顺同志吧,我早就听高连长说了,我们都盼望着你早一天到来。
从此,他担任演出队键盘手,并负责演出队业务。
本来部队文工团是专职的,而演出队都是业余的,可他们有七个人被任做了专职的。
平时都是小型演出,每次都是下边基层连队来大客车把他们连同舞台音响一起拉去,住宾馆,吃酒店,演出结束后再把他们送回来。节假日都是大型演出,就更忙了。
这样在六年的军旅生涯里,他参加了大大小小演出几百次,谱了几十首歌曲,其中有一首‘沧海恋’被海政文工团采用了。
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不让我们去部队看他,在他服役六年时间里,我和他妈没有看过他一次,他在部队花钱很谨慎,千方百计的把省下的津贴存起来,然后问家里用钱不,在转完士官挣工资时,他经常往家里汇钱。
在部队生活期间,他认识了姜昆、李幼斌、谭晶和大连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和老师,并处了对象。
他的对象在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当时任一所私立学校钢琴老师。
他的对象对他说,在部队不能干一辈子,早出来早创业,等过十年后出来就晚了,现在办艺术学习班很挣钱。
他同意了对象的意见,便打电话与我和他妈说了,我和爱人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没有任何文凭,在部队干十年挣个百八十万也挺好,他又打电话给他大姑,大伯,老舅,可都不支持他的做法。
最后他对我们说,我的事情我做主,我谁也不听,我已经和部队请示完了,年底复员。
这时哥兄弟们都对我说,别拦他了,随他吧,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主见。
年底到了,他对我说,爸,我求你一件事,如果我们领导给你打电话,问我复员的原因,你就说你和我妈身体不好,上楼扛不动液化气罐,需要我回去。我说,行。
过几天,他的领导来了电话,是个老夸子,我按照他告诉我的方法说了。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他服役六年后复员了,那年他二十四岁。
他没有回家,直接去了他对象那,二个人坐在电脑前,蕴酿了发展事业计划。
二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从此开始创业,连教学生再卖乐器,用自己昔日攒下的钱,进了各种乐器,大门市暂时租不起,他(她)们先租了个小写字楼,并打出了广告。
教课方法是一对一,每节课四十五分钟,每节课一百二十元。 他(她)俩很有耐心,很有毅力,很有工作方法,也很能吃苦,学员迅速增加,澎涨,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了。
小写字楼装不下了,他们拿着挣到的钱,租了个大门市,雇了六个老师,每个老师每月给开工资四千五。
如果有文艺团体邀请他演出,出场费五百元起线。
他和对象已经登记了,因为忙所以还没有举行婚礼。
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爸,我和对象商量了,从现在开始我给你们和她父母买养老保险,以后我给你们和她父母月月打钱,我对他说,我和你妈现在能维持生活,不用你钱,他说你们挣点钱很不容易,现在我很惦记你们。
昨天我把我的银行卡号给他发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