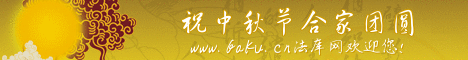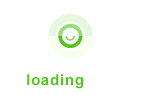尘封旷远的风俗画卷
——孙焱莉短篇小说《扫尘》读后
杨百良
欣然得知孙焱莉的短篇小说《扫尘》荣获2013年度辽宁文学奖,我怀着钦佩和敬慕之情拜读数遍,不由自主地置身于作家所构筑的特定环境中,扮演着小说中的人物并融入乡村一个普通人家,邂逅了一位平凡的女人——腊月二十四,按照习惯,这天她要扫尘……
我所憾动的并非题材和故事情节,《扫尘》写的是寡妇与大伯子暧昧情感的陈旧话题,无论题材和故事本身都不新颖。但她对生活的透彻审视、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以及堪称独特的艺术品格和语言功力,白描般的摹画、生活流的表现方式,使得这个陈腐的话题、信手沾来的家长里短、琐碎的日常生活故事增添了一份鲜亮而浓郁的温馨色彩,酣甜而醇厚的生活涩味。诸如寡妇与大伯子的感情故事司空见惯,很难写得鲜活,被人们视为“理不清、说不明的生活盲区”。而孙焱莉没有过多的理顺与铺垫,亦没有背景说明,开宗明义直面生活境况,单刀直入挑开风俗禁区。
“ 男人走了四年半,是在城里打工没的,从十五楼掉下来。她去看时,人已躺在殡仪馆的床上,走得还算干净,神态还好,像睡着了,看不出一点伤。可她还是哭得人事不醒,昏天黑地。白天黑夜的想了三年,第四年头上她想明白了,人啊!就这样吧。”一位留守的好女人,竟然连留守都成了遥遥无期的奢望。言简意赅的白描写法恰到好处的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故事情节悬念跌起——想着上大一的儿子和七月就要毕业的女儿就要回来了,她还得安稳的日子。婆婆的谩骂絮叨她也视而不闻,因为她心里想着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紧箍在民俗禁区里的男人,在旧屋单独另过日子的大伯子,昨晚回来背着妈妈偷偷塞给她一双暖心的手套。先前的弟媳现在的寡妇,她何曾不知 “宁在小叔子怀里坐,不从大伯子眼前过”的禁言苦果。可她竟然在“禁区”里接受大伯子一双手套,漠大的空间里是彼此心与心的通融。动态语言的白描,把两个人物心爱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巧妙的摹画出生活发展空间,留有深邃的想象和道白,这就是孙焱莉的艺术品格和笔下功夫。
她用动态语言描写吃饭,巧妙的隐喻其内心世界:“秀贤,我前些天去城里买了点壁纸,今年咱扫完房,粘上吧!她愣住了。不光是壁纸的事情,还有名字的事,最重要的他竟然对她说出了这句话。”“秀贤”这两个字只是偶尔在户口本上一闪现,男人都很少叫。而到这时,大伯子突然这么叫了一声,“秀贤”这两个字的寓意和内涵胜过浓墨重彩的刻画和描写,一语升华出男人对她的认知、理解、呵护、爱昧之情。
她和大伯哥扫房的过程写得细致入微波澜不惊。两个人先从房顶开始,一丝不苟,一笤帚一笤帚地扫,几乎不放过每寸地方。扫上了尘,才知道尘是这样厚,这么多。接下来作家笔锋一转:大伯腊月间帮她扫屋,已经坚持十八年了!十八年前的大伯子是个身着绿军装、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十八年来乡村里的流言蜚语、风传绯闻,丝毫没有他们两人的闲言碎语;十八年里的每个扫尘日扫房,都没有引起村人的其他看法,绵长的日子里,他们固步自封恪守民俗禁区压抑着的心头爱火——平静如水的生活岁月,她和大伯子激荡如潮的爱恋激情深深地在各自的心里隐忍了十八年,渴望了十八年!扫尘后铺粘崭新的墙纸,大幅度的留露出两人心中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期翼,表面却依然是平静如初,像十八年来一个又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如此平凡中见奇巧才的表现手法才是成熟作家的真工夫。给她收拾房间,大伯子俨然以主人自居,要把没用的旧东西统统扔掉——挪大柜子时找到了新婚时遗失的心爱的小圆镜子,她不顾一切的竭力吹去灰尘反倒被迷了眼,是大伯子给她察得干干净净的,小小细节激起生活的涟漪,感情的海洋激起的爱的波涛——她的眼里沾染上灰尘,自己清洗不出,眼泪揉干了还仍有灰渣,他心疼了,墙一样立在面前,近,密不透风,没容她表态,一双手一上一下按住她的上眼皮和下眼睑。她使劲闭上一只眼睛,可那只被迫睁开的眼睛看到,他的舌头伸过来,鲜红、灼热;她霎时觉得温暖如春......
人生的坎坷,生活的涩味,世俗的固封,命运的磨难,爱情的纠葛,未来的希翼。一切都在平凡如洗、细微如丝、涓涓流水、波澜不惊的叙述文体中本真呈现。
小说字里行间大片的空白里,是深邃而厚重的传统习惯氛围。两个深爱着十八年之久的好人,历经十八个腊月二十四的“扫尘”,终于打扫得干干净净,扫除了传统习惯的压抑,扫除了民情禁区里的风尘,摹画出的是封存久远的生活样本,激起的是波澜壮阔的爱情涟漪,留给读者的是丰富想象和无穷回味,那将会生发出多么美妙幸福的人生憧憬啊!
值得一提的是,孙焱莉的语言极具特色,东北方言原滋原味地呈现,短促而富有弹性的动态语句,原生态的幽默感,极具感染力,常常让人忍俊不禁。特别是孙焱莉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把握,抒写自如的短句子,简洁明快、留有空白,富有张力。质感而朴实的人物刻画和环境描写,都凸显了小说独有的艺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