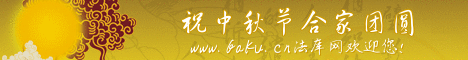核心提示:孙焱莉,生于辽西,居辽北,70后,偏爱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第九届签约作家。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清明》、《星火》、《山东文学》、《鸭绿江》、《山花》、《长江文艺》、《文学界》、《安徽文学...
爱情这朵花开(8)
时间:2020-1-3 8:16:29 点击:
拖拉机
奶奶走了。但是我感觉她还在。她穿着簇新的衣裤躺在地上一个冰棺里,冰棺下面烧着黄纸,烧出的灰烬一包又一包整齐地包起来,码在一起。这是奶奶路上的钱。我很不理解,那个世界连钱都是虚幻的,若世界是虚幻的,那怎么能算作世界?后来,我又想,如果这些钱真能花,奶奶会用这些钱买什么?我妈常说,你的出生要感谢你奶,我们一家人能见到你也要感谢她。我初为人形时,正赶上计划生育。本来我的出生应该是没有波折的,可这浪潮一来,我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一个不该出生的人。那时村头的墙上到处写着标语,突然多了一些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他们握着生杀大权的刀柄,把我划归为一个多余的人。他们到处宣传,挨家挨户查看妇女们的肚子。他们到我家时,我奶奶第一个迎出了门。
那时奶奶端着个盆出来,迎着刚要进门的人,一盆泔水泼出去,计生干部的鞋和裤子顷刻湿了。
然后我奶说,哟,没看见有人来,知道有人来,这盆泔水就泼到猪圈去了。那两个人弄了一身脏,又说不出什么来。
我妈常描述这一段,说到这,她总吃吃地笑,仿佛这是特别快乐的事。每到这时,我心里总有一个小声音在对付我妈的话,这事应该你干,你应该拿泔水泼计生干部才对。但我妈从来没有听到过,因为我没说出口,毕竟是她生了我。我妈是个天生软弱的人,她一辈子听别人的,听她爹妈的,偶尔也听我奶的,听我爸的,听我们的。
我出生的曲折历史是在我妈我奶的陈述中完成的。
我奶说,那时节,种完了地,都闲起来,计生干部老是往咱家跑,我一看就恼,恼得不行,就想找人打架。俺们自己家的骨血,你凭什么说扔就扔了,说杀了就给杀了,简直是刽子手。可你爸妈那时也犯起糊涂来,真是急死我了。
我妈说,其实我和你爸也舍不得,可后来看别人都那么做,想反正前面有三个小子,心里有底,少生一个就少一个吧,再添一口人又多一张嘴,就随大溜儿吧!我妈像说别人的事一样淡定,我斜着眼睛看她。
我妈怀我五个月时,终于被村干部动员去做流产。拖拉机斗里或站或坐的,有七八个怀孕的妇女,那真是奇观,后街二婶说起那情景笑得嘎嘎的: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大冬瓜。我能想象车斗里坐着一个又一个大肚子、小肚子浑圆的女人,多数人脸上都是顾虑重重,也有两个嘻嘻哈哈像赶集一样快乐。
我妈是最后一个上的车。我妈上车后,开拖拉机的人摇着了拖拉机。拖拉机“突突突”地憋着一股劲儿,像一匹打着响鼻儿的驴子,看那架势一下子就能蹿出去。就在这时,奶奶出现了,没人看见奶奶什么时候来的,好像她一直伺机等在拖拉机的车底。车要开动时,她猛然就出现了。
奶奶以匍匐的方式,把两只手长长伸到拖拉机的头上。奶奶说,谁要把我孙子抢走,我就死在这里!
车上的计生干部下来拉奶奶。奶奶一骨碌坐起来,又双手伸进轮榖里,死抱住轮胎。轮榖空隙小,奶奶的右手手背卡破了,血流到她的灰裤子上。
奶奶两手相扣,没人能掰开,他们也不敢真的使劲掰,怕她下一步继续做什么傻事。做掉一个孩子是小事,那只是一小团蠕动的肉球,而这样一个老太太,全胳膊全腿,会哭会笑会骂人,儿女一大帮,出了事,谁兜得起?没人真敢把她怎么样。
后来计生干部让我妈下车,说下一批再跟着做,反正月份也不大。于是,我妈下车跟我奶奶回家了。
再后来,计生干部没有让我妈做人流,她们似乎把我妈给忘了,只是在我出生后才来到我家收罚款。
我的出生因为不合理被罚了三百块钱。我奶拿出二百一十元,加上我爸的九十元,我的出生算合理,上了户口。
后街二婶说:拦拖拉机时,你奶没骂人,也不吵嚷,以死相挟,要换回孙子的命。你奶奶认定你妈肚子里是个男孩,不但把你妈从车上硬拉下来,和计生干部撞羊头,还数落起那几个要做流产的妇女:你们这些个狠心的娘啊,你们的孩子投奔你们来了,你连个活路都不给他们。那几个做人流的妇女如今每次看到我,就会想起或念叨着她们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
有一次,大概十六七岁时,我问奶奶,知道我是个丫头你后悔没?奶奶说,后个什么悔哟,我一看你妈那身形就知道准是个丫头片子,我就想要这个孙女。我就喜欢女娃,一辈子从身子到心都能花枝招展,让自己喜欢的男人疼,为他哭,为他开花结果,生根发芽,多美!哎!你都不知道你爷爷有多好!再大点你就明白了。我就搂着奶奶,把她的额头和脸颊亲得满是口水,奶奶边“咯咯咯咯”地乐,边躲。
奶奶要停放三天,等待人们的吊唁。
按当地的规矩,我是不能在葬礼上出现的。
可我不顾众人的反对硬跑过来。徐小平这次也拦住我说:要不咱不去吧!我说不行,怎么样我也要给奶奶烧两张纸,让她知道我来送她。徐小平说她已经走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她知道,她看得到。在我的感觉里奶奶一直都在,即使她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她还是能感知一切的。
我在绝望里跪下来,为奶奶深深磕了三个头,我的额头上沾满了纸灰,我的眼泪什么也不抵,只是让悲伤更具象了一些。
我很快被拉起来,拉走。有人为我擦拭额头上的灰,有人给我拍掉新裤子上的尘土。虽然不多,依然有人细致地给我收拾好,还有人体贴地给我擦眼泪。有人在我的手腕上绑上红绳,这些就源于我是新娘。想起当初,我奶奶头抵着拖拉机轱辘,在雨后的泥地上跪着,坐着,甚至躺下,换回我的肉身,招回我的魂魄。当时没人给她拍打,擦拭,但是她内心里一定充满欢喜。二十五年前和二十五年后,我们祖孙俩同样是爬起来,心境如此迥异。
我继续我的新婚日子,他们集体把我阻隔在葬礼之外,让我与这场葬礼不发生关系。这次,徐小平的父母非常热情地把我接到他们家,说徐家的希望在我身上呢,千万要保重身体,保持精神愉悦。徐小平的母亲是教师退休,说出精神愉悦这样的词语一点不足为怪。我却不能因为她的一句话愉悦起来,依然心情低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的脑袋像电影放映机一样播放着从我记事起奶奶各个时期的影像,正面的,侧面的,还有远远近近的背影:走着的,说着话的,嘎嘎大笑的,缄默不语缝衣服的;给我梳羊角辫时吐口唾沫再用手抹光,唠唠叨叨往我包里塞钱;抱着车轮躺在泥地上放赖,领着我妈往家走,回头诡秘一笑,对我和一车的南瓜说,你们会后悔把四丫头杀死;在炕里盘腿缝着缝着一个小花裙子,突然探过一张褶皱不多的脸,那时我还蜷缩在大水茫茫的河底,她隔着堤岸和大水朝我一笑,说:一切都会过去……
我烧了两天,第三天醒来病好了。
奶奶出殡后,我正好回门。我去奶奶屋里转一圈。现在,奶奶的屋里空下来,所有奶奶用过的喜欢的东西都不见了。只留下一个老柜,斑驳地立在阳光地儿里,把泼进来的几大片阳光也弄得新旧不一。屋子里很静,但我依然感觉奶奶坐在那,手里转动着她的银镯子,她那如梅花艳红的指甲真是美丽。还能看见她在地上慢慢走动,走到窗台边,拔掉盆里的几根草,她用木梳沾着清水梳头,梳得白头都有了一丝丝黑和光泽。
奶奶最后说:都会过去!这是她给我的遗言。
摸着手腕上温暖的玉镯,我的心彻底坦然平静下来。
奶奶头七,我和徐小平回到了我的新房。在隔壁,他们在举行一些仪式。
那晚,我和我的男人徐小平,洗漱完毕,钻进那床红被子里。他的手在我平滑的小腹上来回抚着,食指和中指交错地轻轻扣了几下。他眼睛深情地注视我。我心领神会,环起胳膊,搂住他,衔住他多肉的嘴唇,把自己打开,怒放,收拢,把这世间和奶奶的世间都关在了爱欲之外。在我努力向上攀登,不敢回望,不敢懈怠,死死抓住那个藤蔓与枝丫时,我感觉山风与洪水即来,濒死的坠落即到,我万劫不复的罪恶与哀愁即要把我吞噬。猛听到身体里“叮咚”一声轻响,仿佛有人在敲门,我拼尽最后的力气打开门,在万念皆无时,一个孩子站在门外朝我笑,喊,妈妈——那个时刻正是我奶奶上旺的时候,一支燃了大半的香从直立的墙壁上“吧嗒”掉下来。
我的奶奶彻底走了。
作者:孙炎莉 来源:网络
相关文章
相关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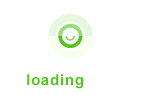
发表我的评论






























- 大名:
- 内容:

本类热门
- 04-13·沈阳选美比赛 13名佳丽美胸长腿秀不停
- 01-03·爱情这朵花开
- 05-06·2015国际旅游小姐大赛驻马店赛区总决赛
- 03-15·辽大汉服女生走红校园 爱武侠爱古典文化
- 06-02·最心酸的儿童节礼物 她偷了个鸡腿给生病的女儿
- 03-15·婚恋观调查报告:沈阳性态度最开放
- 04-10·沈阳女孩辟谣与空姐艳照无关 原照片为伪娘照
- 02-14·女子约会无业游民被拍裸照 打电话给女儿求救
- 06-17·沈阳明日迎最大规模停电 市内多路段受影响
- 09-28·无腿女孩以手代步求学12年 大学免除其4年学费
本类推荐
- 没有
本类固顶
-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