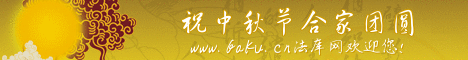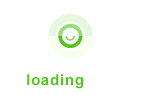——读孙焱莉的小说近作有感
作家在写小说时应该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感觉器官,你的味觉、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触觉,或者是超出了上述感觉之外的其他神奇感觉。这样,你的小说也许就会有生命的气息。它不再是一堆没有生命力的文字,而是一个有气味、有声音、有温度、有形状、有感情的生命活体。
——莫言:《小说的气味》
一
未曾谋面,也没有就有关文学的话题进行过交谈,只是读了她的四篇小说,《命犯桃花》(载《鸭绿江》2009年第2期)、《少年商榆的春天》、《眩晕》、《洞天》,和她的一篇创作谈《让气息拨动你的心弦》,就开始我的“说三道四”,对于这些作品的“建筑师”孙焱莉而言,是有失厚道和公允的,这份歉疚,请有着“一颗敏感、警醒之心”的小说家见谅。
从孙焱莉的小传中得知,孙焱莉出生在辽西阜新市彰武县,属70后作家群中的一员,也是辽宁文学新锐作家班第五期学员中一员。依我的经验猜测,孙焱莉的学生时代是“重文轻理”的,常常睁大眼睛看周围世界的她,作文是被她的语文老师看重并经常当“范文”的,小小的得意后,同伴们的羡慕与嫉妒也相伴而来。敏感的天性使她对身边的生活多了几分“觉知”,而对生活细节的记忆能力,也为她后来的小说写作储藏了更多的“柴米油盐”。虽然有过“少年才女”之名,但出于对文学“先天”的情有独钟,使她对文学有了几分真诚的敬畏,正是这种敬畏,使她在本可一展才华的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写一个字”,但正是这个年代的“内敛与静观”,让她的“文学内功”,得到了磨炼,使她如一粒吸足了养分的种子,她的吐芽、开花、结果,也就有了必然的理由。
二
在小说《命犯桃花》中,孙焱莉捕捉到了被她所强调的“小说气息”,在小说的开篇,作者颇费了一段心思,甚至尝试几种不同方式,当她完成了如下的文字时,她如同在布满铁屑的生活场中,投下了一块重重的磁铁,语言带出了情节,也带出了一段“多米诺骨牌”般的底层叙事:
莫金在前面走,小梁落在后面,很远。太阳仿佛就在他俩一前一后的脚步里“啪嗒”一声,落下去了。小城的傍晚有雾悬浮,屠宰场的上空烟尘滚滚,天昏暗得如飞般快。
有狗叫。
在这样的气氛中,小说中的两个如影随形的“主人公”走进了充满了血腥气的陌生之地——一所小城的屠宰场。
同是挣扎在底层的“难兄难弟”,只因哑巴小梁眼巴巴的无助的凝望,莫金便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放心,有我呢”的“承诺”。屠宰场不是人间的天堂,杀戮是这里每天上演的主题。小梁对最初的“工作”是不适应的,望着没被杀死的鹅挣扎着跑几步“然后猛地栽倒”,此时,“小梁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后来就干脆蹲在地上,头缩在双膝上‘伊伊啊啊’地哭”。但环境却改变了小梁,使“小梁成了一个合格的屠夫”,“眼法、手法、刀法准确到位,活做得干净”,不仅“记住了厂棚里所有拔毛女人的面孔”,还发现了第一个出现在大厂棚的“面若桃花的女子”——秀松。因为秀松,小梁得罪了“悍女”张九九,若不是莫金的阻拦,一场“人命案”将会上演;因为“食堂女人小窝头”,小梁初尝“禁果”,可最终的结果却是“泪流满面,一夜无眠”。当“太阳照常升起”后,小梁因为“十一只鹅”的出现,才被“从绝望的境遇中搭救出来”。但好景不长,当“拎着鹅”的小梁与“小窝头”互相凝望时,惨剧发生了,一堵红砖墙夺去了小梁年轻的生命。莫金的诺言落空,痛哭起来的莫金也“不知道小梁的命到底犯给了谁”?不难看出,《命犯桃花》是孙焱莉精心建构的一篇小说,在拨动读者心弦的同时,也将她的创作主张很好地表达其中:“生活孕育了小说的形状,思索成了小说的筋骨,经验令小说有血有肉”,而“寻找小说的灵魂”的弦外之音,却留给了她的读者。
读《命犯桃花》,在领悟着“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的阅读体验中,哑巴小梁的形象,在我的眼前逐渐丰满起来,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底层写作”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形象”,一个“守口如瓶”,“惟一相信的只有自己的一双眼睛”的小梁,他在带给人们“底层的忧伤”的同时,他的善良与单纯,他的固执与冲动,都是鲜活可感的。
我觉得,面对中国当下文坛,孙焱莉用她的小说《命犯桃花》,在进行着一种努力,一种“抢救人物”的努力:“既然人物是小说的中心,小说的生命,现在眼看着活生生的人物被现实所压抑、所窒息,作家们当然应该义不容辞地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人物。”(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我相信,孙焱莉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
在世事的因果之网中,织出的不幸与苦难似乎总是多于甜蜜和幸福。而如何面对这些,人们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在小说《洞天》中,一位乡村的待嫁女路水水,在一个黑夜中埋下一粒“邪恶之种”,“由于不能做流产”,“当这个埋在体内的耻辱之果‘砰然’落地后,她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浸在泪水中的路水水看见了什么?“这是一个那么柔弱的小东西,他仰在那儿挣扎着,细声啼着紧闭着眼,似乎不想面对这个光亮的地方。”当路水水母性的本能被唤醒之后,当“她感觉这就是另一个自己”时,她说服了准备“弃婴”的父亲,选择了“从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边门店老街叔叔遗留下的老屋里“开始忘记”。路水水不是圣人和智者,但她却和相依为命的儿子望天儿,倾听着如同先知般的劝说:“当黑暗和绝望来临,我们必须愿意正面遭遇它,勇于面对面;甚至,若有必要,还得一遍又一遍,既不避开,也不编织千百种方法来摆脱那些摆脱不了的,或足以麻痹自己来逃脱。”(乔·卡巴金语)路水水用自己的行动和承担,收获了她“禅悟”般的活在当下的体验:
路水水……第一次把自己放置在老街的路中央,放在如刀锋般闪烁的太阳光下,放在一个门,一个洞的面前,她要看看所有躲在暗处的人。
路水水第一次用如此犀利的目光看边门店老街的人。那一时刻的感觉是那么美好。不用畏惧,不用担忧,简直就是一块不可撼动与入侵的石头。她的邻居抬身向院子里逃去,另两个男人转过头不看她。
路水水趟过了人性幽暗的沼泽地,当她发现人性尊严的力量后,还收获了一个男人胜国良的爱情,她还被老街开杂货店的姚娘认定为“不折不扣的妹妹”。更让她欣慰的是,让她收获了因仁义赢得伙伴尊敬的——我不叫望天儿,我叫路小峰——由“野种”而重生的儿子。
《洞天》的文字是不乏诗意的,可诗意的背后,是人与人的纠缠与被纠缠、折磨与被折磨。但孙焱莉是冷峻的,她用“理性与犀利的笔”,剖析了“社会中的林林总总”,她的写作才华,也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展现。
读《少年商榆的春天》,在小说家针针线线的编织中,我读到了一种“密不透风”的压抑之气,几次的跳进跳出,十四岁的商榆让我想到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商榆的成长有着独特中国要素,在一次次的争吵中,在一次次的出走与返回中,敏感的商榆经历的实在太多太多,这是一篇中国版的“少年成长小说”。我们可以证明的是,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在中国的适用。但让我眼前一亮的段落,却是孙焱莉笔下对“死亡”的从容的“轻描淡写”。透过一个十四岁少年的“内心宁静”,让我看见了一个扎纸活老人的“看透与宽容”,让我想到先哲庄子超然的“鼓盆而歌”的现代版:
少年商榆不喜欢任何抬出自家院子的花圈与纸活物件儿。……那些花朵物件儿只有在他爷爷手里才出生时才是纯粹的,才是短暂一生中最美好和绚烂的时光。老天爷不收人时,那些洁净的花圈就在自家的厢房棚子里摆上几日或多日,然后突然某一天被买家拉走,或如果是近处的街坊邻居及人家有特别要求的,商榆就送去。这活儿商榆从十岁就开始干了,经过四年的时光,商榆已把死亡尽收眼底。
因为有了这样独特的生长经历,少年商榆以他的率真之眼,发现了“生死之间”的玄机与真相:“他能镇定自如地迈进每个离死亡最近的院子,他常不经意地从外间堂屋或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这样的情景:死去的人被蒙盖着,脚挺挺地支着,露出一双怪模怪样的厚底鞋,像棉鞋一样笨重。活着的人总不顾死去人的想法,大热天儿也要给穿戴好几层衣裤,想必另一个世界是没有夏天的吧。”少年商榆用他所亲历的生活,开始了他一己的思考,他不再人云亦云,他的清醒与早熟,使他向成人世界的混乱与盲目,提出了大胆的控诉与质疑。少年商榆的存在,像一面镜子,让人反思这个患病的现实社会。孙焱莉也如同一个拂去镜上尘埃的“小说巫师”,给她的读者照亮了一条透视生活的通道。
四
2008年的初秋,我曾有幸和我的母校辽宁文学院新锐作家班的学员们,进行过一次文学交流活动。在这次交流中,我推荐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和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读孙焱莉的小说,不由得让我想到了赫拉巴尔的作品和他的创作主张。在孙焱莉的小说中,不论是小城、小镇、小村,她笔下的人物更多的是“小人物”,更有小人物中的受辱者、“智障儿”、离异者、边缘人,她关注的是“弱势中的弱势”、“底层中的底层”。因为选取生活视角的独特,孙焱莉的小说很自然地带上了“底层的气息”。在她的作品中,她的底层视角也多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成长中的孙焱莉,是可以预期有“小说前程”的一位作家。
因为对孙焱莉的小说创作有所期待,我愿把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向她推荐,也愿把赫拉巴尔的一段创作谈与她分享:“在我的作品中,最大的英雄是那个每天上班过着平凡、一般生活的人;是我在钢铁厂和其他工作地点认识的人;是那些在社会的垃圾堆上面没有掉进混乱与惊慌的人;是意识到失败就是胜利开始的人。”
在读过了孙焱莉的《眩晕》后,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她的“短篇小说”的篇幅是否“过长了一点”,如果有所“瘦身”,也许是别样的景象。我觉得像《眩晕》这样“人物较多的小说”,作者下笔前更应该周密布局,使“遗憾”降到最低。可我更想说的是,这样的题材是可以进行中篇小说创作的,如能从容开掘,以作者的“气息说”而言,更深地拨动读者的心弦,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若不信,请读孙焱莉此后的小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