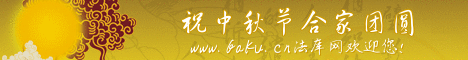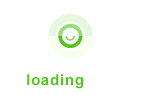石熊山,首见于《辽史》中,在“宗州”下记载:宗州“在辽东石熊山”,同时宗州还辖一县,为:“熊山县”。这些记载很明确,石熊山在宗州,并因该山而名县,遂辖有熊山县。
但《辽史》记石熊山不详,仅说“在辽东”,只有大致方位,不够具体,在辽东何处确难于寻觅,据此还无法确定下来石熊山的具体位置。
关于石熊山的记载,文献中也有涉及到的,且时间较早,这对探讨石熊山所在很有帮助,现为列下。
检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北藩地理》中,载有:“宗州,治熊山县,在熊山之阳,东辽水,南至显州一百里。”曾公亮记述较《辽史》为详尽,并列有较稳定的参照物,即“东辽水”,说明石熊山在今辽河之西;宗州“在石熊山之阳”,山南为阳,说明宗州在石熊山的南面,宗州之北即石熊山;宗州“南至显州一百里”,显州为今北镇市,说明宗州与石熊山俱在今北镇市的北面。石熊山在辽河之西,山前有宗州,其地又在今北镇市的北边。有了这些较为具体的方位,则石熊山就可进一步寻求了。
从上考可知,石熊山在今辽河之西、北镇市之北,其地当在今法库县境内。明代《辽东志》记载:“熊山,(开原)城西北一百九十里,在辽河西岸。”熊山,即石熊山,辽称熊山县即是明证。《辽东志》在此不仅记录了其方向,在开原之西,开原之西即为法库,而且还标明其里距,为一百九十里,从开原老城到法库镇,考虑实际道路迂曲,两地相距为一百四十余里,再西四十里至四家子村,其里程恰合。由此可定点石熊山为今法库县西之四家子村一带。
明代《辽东志》又载有一条重要道路,系经过石熊山:这条路是由当时的开原(今开原市老城镇)西去懿州(今阜新县塔营子村)的道路,中间经过的驿站,具体站名排列为“庆云站──熊山站──洪州站──懿州站”。熊山站,就是设在原辽代熊山县址上的,也就是石熊山所在。如果考察这条道路经过“熊山站”各站点的分布情况,则石熊山所在也就清楚了。它们的情况分别是:
庆云站,此站其地为辽时祺州,其州辖一县名曰庆云县,金灭辽后,废州存县,仍名庆云县,至明时成为驿路站点,名为庆云站,其地经笔者考古调查发现并考证为今康平县东南境郝官屯镇辽河西岸的小塔子村辽城址。
熊山站,此站其地为辽代宗州,该州辖一县名为熊山县,金灭辽后,州县俱废,降为村寨,至明时成为驿路上的站点,用其名为熊山站,其地经笔者考古调查发现并考证为今法库县城西四家子乡四家子村古城址。
洪州站,此站其地为辽代横州,因系头下州未辖县,在金灭辽后,州废,应是降为村寨,故《金史》在建置中未载其名。至明时,驿路上设为站点,称为洪州站。李文信先生在《全辽志》的“开原西路陆”站点下批注:“洪州,当是横州之讹,横州为辽头下州,州有横山因以得名,在辽州西北九十里,今彰武东北土城子。”笔者对彰武县苇子沟乡土城子村古城址进行过考古调查,是一座典型的辽代城址,结合文献记载,该城址为辽代横州,后世讹为洪州,遂失原名。
懿州站,此站其地为辽代懿州,原为头下州,不辖县,后进献国家为行政州后,辖二县,由于州县迁治,情况较为复杂,多有考证,然皆未得其实,笔者曾至实地详加调查并为辨证,其地为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北境的塔营子乡塔营子村。懿州,为这条路上西端的一个站点。
按明时这条由东北向西南、起开原终懿州的路,是一条古老的路,起源甚早,辽代所建一些州、县城,都是由这条道路联系起来的,前后并多见于行程记载。如果我们今天作实地考古调查,仍能看到这条交通道路的历史面貌:从开原老城镇西南行,过辽河,至康平小塔子(辽祺州、庆云县),然后西南行进入法库县,又循路向西南行,经今关屯、黄花山村,凤岐堡、大房申村,到法库镇,然后由镇西去,沿巴虎山南麓山谷中东西通道至四家子村(辽宗州),经大屯,又西南行,至五城店村(辽灵山县)、南土城子村(辽原州),此后西行,进入彰武县到土城子村(辽横州),再西行,抵达阜新塔营子村(辽懿州)。很明显,这条道路确定下来,宗州所在位置明确,文献所说的宗州在“石熊山之阳”,则石熊山即可不言自明了。
宗州既是处在四家子村北作东西走向的八虎山脉一个山岗的南坡上,而石熊山亦因此可知即为今四家子村后的八虎山,对此无可怀疑。
上面这个结论确定之后,是否从山名上也可看出二者之间有传承嬗变之关系?如辽代石熊山,今天称八虎山,它们是否一致?
在我国山川地名变化上,常存在前后相联系的特点,名字不是突然产生或完全不相干的改变,总是有一些缘由的。这种事例很多,今举一地域较近的事说明,以便更易于理解。原属法库现为调兵山市的山名变化就是一例。历史相沿,在明代和明以前,今调兵山市有两座山,一座叫刀山,一座叫跸山,这在明代《辽东志》上记得很清楚,该志卷一《地理》山川“开原”下载:“刀山,(开原)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辽河西岸。跸山,(开原)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辽河西岸。”二山俱在辽河西岸,其地属今调兵山市境,由于二山都是单字名,又因二山相距很近,就常被人连称为“刀、跸山”。这种情况到了清代以后,事情发生极大变化,真是出乎人们的想象,刀跸山衍变为“调兵山”。随后,调兵山又和金兀术联系上了,村庄也出现了兀术街,这里成了“金兀术”灭辽调兵的地方,并且相应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民间历史故事。实则这些变化是毫无依据的,但有所本,因此它不是凭空想象生出、而是还有些缘由的,这就是一种嬗变关系。再举一例,如大家熟知的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所在的丹东市宽甸县那座山,明以前称为“马耳山”,此山是明长城所起,因此明臣巡边给朝廷奏疏如王之诰、李辅等,都亲历此山,历史久远,但后世却叫成“虎山”了,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称呼。马和虎,虽有区别,仍是相类动物。
在此前提下,石熊山与八虎山这个名字,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它的嬗变来,因二者名字有太大的关联。辽代称此山为石熊山,后世改叫八虎山,熊和虎从种属上说更近,较马与虎的改称要容易得多,而由熊转为虎,应是更为普通的事。于是早期的石熊山到后世就转称为八虎山了。但现在法库当地还有一说法,认为此山叫巴尔虎山,系蒙语,其得名是由蒙语称呼。对这一说法,我有个人意见,认为这是它的又一次嬗变,由于“八虎山”一词和蒙古语“巴尔虎山”音近,当地又居住有蒙古族人,人们因音近就说为巴尔虎。实则八虎山应是石熊山嬗变后之名称,而巴尔虎山之名则是后来附丽上去的。